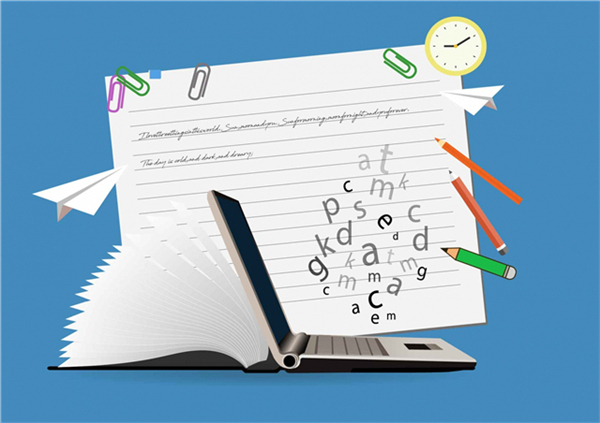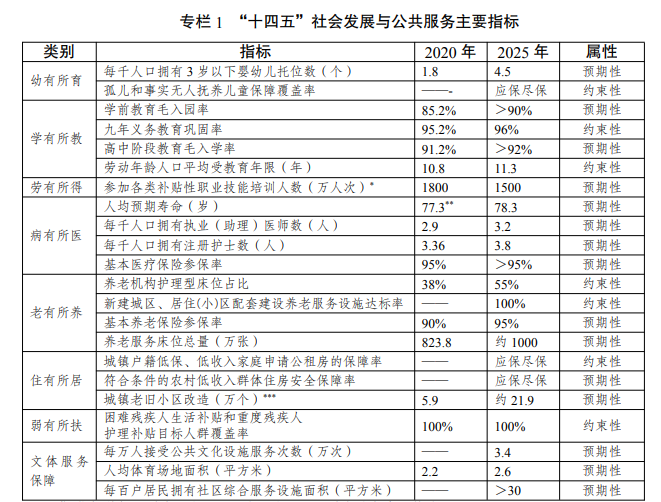+++
标题图转自流星r大佬
+++
 (资料图)
(资料图)
第二章
————————
生而复死
药剂师
苍白之王
他死过的次数他已然数不清。周而复始,他感到自己心跳停止,而这股痛苦无法承受,但凡他还能喘进气来他一定会尖叫出声。
那是在虚空中曾经所发生的,那段时光感觉似乎是永恒。也可能时间更久。兴许他的一部分永远留在了那里,死而复生,然后再次死亡。有时他无法分辨这些状态——它们融为一体将痛苦延续。某种程度来说现在一切都已经结束了,但他依然被夹在那种中间状态,仿佛他的灵魂从未真正逃脱过毁灭大能,被其邪恶攫住轻轻压成了容易摆布的浆糊。
但在其他方面他又回归了熟悉的常态。他可以再次举起武器蹒跚的向地平线走去,为他的原体而杀戮。他可以服从命令,下达命令。他是一名士兵,就像年轻时在巴巴鲁斯一样。一名反抗暴君的斗士。
所以凯法·莫拉格(Caipha Morarg)虽说彻底转化了,但也完全没变,外表被重塑而思想一如既往。他再也无法脱下甲壳般包裹住自己的盔甲,这是实话,并且他只能喘息着呼吸,眨眼时也不会在眼球上留下粘液,但他保持了自我,一位原体的忠诚侍从,一名军团的仆人,有朝一日将记录历史的一位观察者。
他抬起沉重的头,感受腐烂战甲中伺服器被卡住的咔哒声(catch and snick)。到处尘土飞扬。灰尘搅动着被轰炸撕出一条条裂痕的废墟,淤积在灰黑色沙丘中半倒塌建筑物的地基上。这种情况下根本看不清远方。一名凡人最多看到几十米开外。他自己透过现在将眼中一切都染成绿色的滤镜能看的更远。他辨认出远处科比尼克堡垒的废墟,一堆倒塌的砖石结构在飞来的弹药作用下炙热依旧。较近处,几公里外皇宫墙上矗立的巨像之门(Colossi Gate)被熏黑且受损,但依然傲然挺立。山峰间的废土满是被夷为平地的房屋和工厂废墟,低洼的碎石如今堆出了迷宫。
就在他张望时,有什么东西在昏暗稀薄半透明的光线中闪闪发光。一张脸从尘云中浮现出来,短暂地拉长,滑落,凝固成一个膨胀,下巴松弛的生物,就这么突兀的在余震中完全现身。它颤抖着,在现实中滑进滑出,随后溜进阴影里寻找可以大快朵颐的东西。
莫拉格还不习惯它们。恶魔们。以前的他光是嗅到这种恐怖之物的气味就会发自内心排斥,而现在它们遍地都是,在敞开的门道间穿梭,在被炸毁的街道中嬉戏,它们从土里现身,在空窗框上蠕动爬行。有些沉默不言,有些一直低语。有些会以动物形象现身,所以你永远无法确定什么是真实的,什么不是,直到你足够接近能嗅出异样。还有一些则巨大而令人生厌,在尘云中摇摆不定,高耸在下方军队之上。它们还是会遇到麻烦。越接近大结界他们的情况就越糟。哪怕现在,即使堆积如山的痛苦已铺天盖地的压向帝皇的灵能防御,它们依然无法完全越过最后的防线。在有些事情上它们仍然需要血和肉。
但现在看来用不了多久了。漫长的皇宫内城周遭的每一堵墙都在受攻击。轰炸从未停止过。压力从未减弱一丝一毫。敌人手中所剩微不足道的领土正在被压缩、挤压,越来越狭窄,直至像腐烂的水果一样裂开。然后恶魔们就会真正的开始工作。然后他们就会无拘无束地狂奔,享用废墟中幸存的灵魂。
在有些日子里,当莫拉格想到这一点时会郁郁寡欢,忆起他的职责曾是追捕怪物而非协助怪物。在其他日子里,当战斗唤醒他灵魂熔炉中已冷的炭火,他只想要看到它,享受它,在众神的幺子们行使它们的神圣职责时露出恍惚的微笑。泰丰斯(Typhus斑疹伤寒的意思,真正的死亡守卫原体,著名大孝子,说好的大家是兄弟,有一天突然兄弟变成了爹)——他们不得不叫他泰丰斯——不停的宣扬教旨,告诉他们命中注定他们会变成这样,永远不要后悔做出的牺牲,当他们还是巴巴鲁斯上的流浪汉和可怜虫时,神明心中已经有了他们,一直知晓他们可以变得更有价值。
莫拉格回想起这段记忆微笑了起来。更有价值?从某种角度上来说他们确实是。现在很少有东西能真正伤害到他。爆弹可以射穿他的盔甲,刀刃会深深咬入他腐烂的血肉,但他能迅速恢复,仿佛就在亚空间时那样,死而复生,生而复死。然而他怎么可能忽视所有这些力量可见的代价——他的皮肤因肌肉萎缩而松弛,他的毛孔渗出黑色油腻,他接触的所有东西似乎都因腐蚀变厚并开始溃烂?如果这是一种赐福,那也显得很古怪。如果这是一种嘉奖,那它尝起来颇为苦涩。
他听到了远处枪声奏响了轰鸣。他感到脚下大地在颤抖。那些神之机械还在行进。他知道它们此刻正在墙角。现在正是一个时刻,一个转折点。一旦形成第一个缺口,所有其他的缺口都会接踵而至。他希望自己能在那里,在遥远的卡塔巴蒂克平原(Katabatic Plain)上,见证死亡军团(the Legio Mort)摧毁最后一道物理屏障。随着东北地平线上的尘云不断增长,大地和天空间形成沸腾的柱子,他想象着它们所引起的恐慌并开始咯咯笑了起来。
这使得他满是痰的喉咙哽咽,他咳了一声停下来。现在他的身体连让自己愉快的哈哈大笑都做不到。一种交易。一种合约。然而,这并非他做的决定。原体替他们做了决定,虽说原因仍使他困惑。人必须要有信念。莫拉格并不怎么信神,但他依旧信任在巴巴鲁斯上拯救了他们的那个人。
他又开始行走,抬起一只泥泞的靴子,然后抬起另一只。他需要一段时间才能到达要去的地方,但这对他来说没问题。他已经经历了永恒,曾经到达了宇宙的尽头又返回,死而复生又死去。
这会让人更分得清轻重缓急。在那之后,在这一切中,当冷漠的宇宙将原始地狱端到你面前时,你得学会看到有趣的一面。
每次杀戮后,他有时内心会思索,想知道自己是不是第一个接受这想法的人,多笑笑有好处。
这一切都太迷人了。一个新世界,像一朵盛开的花朵般绽放,一切尽在他掌握之中。
扎达尔·克罗修斯深吸一口气,品尝并感觉它。他的身体做出了反应,吸收了每一种新的感觉,吸收了这一切,感受到了一些他无法用语言来形容的东西。天空是深灰色,烟雾弥漫弥漫。大地是黑色,空气中都是灰。每一块地表,每一块砖瓦全布满污物。然而,如果你跪下来,把头盔挨得足够近,你可以看到那里的区别——微小结晶碳的闪光,昆虫爬过泥土,尽管到处都是毒素但仍在苦苦挣扎。克罗修斯会伸出手用一根手指玩弄它们一会儿,然后碾碎它们光滑的甲壳。
他以前曾是名药剂师。曾几何时,当世界依然枯燥且恭顺,他大部分时间都在修补伤口和骨头。当时他自以为知足了。星际战士是一种惊人的存在,除非极端灾难的环境否则大部分情况下都能自我修复。十四军团的战士即便用相当高的标准来评判也非常杰出,他们具有极端的身体耐力。那些来自巴巴罗斯的人树立了榜样,他们一直生活在一个充满毒素的星球上,而泰拉人很快迎头赶上。讯息是从最顶层传来的,自原体而来,一遍又一遍被传颂。
你们是我的不败利刃。你们是死亡守卫。(You are my unbroken blades. You are the Death Guard.毒气罐很爱护子嗣,崽崽们也很信爹。莫塔里安对儿子们那么包容,升魔也多少出于心疼崽们。像伽罗那样有独立思维依然忠诚帝国真的很难得了)
事后来看,克罗修斯好奇自己怎么会在过去那种生活中获得乐趣。的确,这个职位很光荣——在十四军团药剂师的地位就像是第十军团的技术军士,负责照看军团那令人艳羡的特长。但他照看的对象是如此阴郁和冷酷,如此……一成不变。他们从来没有对他微笑过,也没有向他表示过感谢。他们仿佛被乌云笼罩,这种沉重感仿佛石头一样呆板,油一般枯燥无味。
现在,不过。现在。
他一瘸一拐地穿过起伏的地面,靴子深深陷在泥土里。每一个动作都激发了疼痛,但这种疼痛如此有趣,他仔细思索着发出惊叹。他曾经引以为傲的身体现在正逐渐崩溃。他肌肉松弛,皮肤苍白。当他旋转身体时,盔甲发出抱怨声已经开始失能。蜘蛛状的的彩色铁锈爬满盔甲的金属表面,他已经放弃了冲刷。最好让其全部降解,滑落成一团油腻。你可以真正享受其中——解脱!从所有无穷无尽,无穷无尽的苦差事中解脱出来。
现在他的思维方式不同了。他注视着他的兄弟们,看到他们也在变化。他们就仿佛孩童般,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,每个人都小心翼翼地行进,逐渐发现自己转化成了什么,以及即将变成什么。在这颗一切开端的星球上发生这些简直恰到好处。军团已经散布整个银河系,发动了200多年的沉闷战争,而现在再次回归,被改进,被解放,登临了超越想象的奇迹顶端。
“药剂师”一词已经不太合适了,他想。必须编造出更好的东西以更接近地反映现在可能的生物学探索。但旧的称呼临时也够用。毕竟还有一场战争正在进行中。
“克罗修斯!”身后传来一声大喊。
他转过身来,看着一支装甲纵队从雾中逼近,在旁边追赶上了他。一群衣衫褴褛的暴徒组成的步兵正在行军,破布挂在暴露的皮肤上,表情空白而失焦。满编的战斗兄弟们,那些仍然自称不败者的,与可怜虫们一同行军。他们现在是肿胀的生物,盔甲关节处浮肿,他们肮脏的陶钢蜕了皮。一排军团坦克在不平的地形上摇摆,密集的浓烟排放到已然可怖的大气中。咆哮着的重型车辆沿着道路行进,最后消失在袅袅薄雾里。克罗修斯停了下来,等着向他打招呼的人从舱口钻出,吃力的走向他。
格雷姆斯·卡尔加罗一直是个沉默寡言、自闭的人。在大叛乱的最初几年里,他曾担任军团舰队的军械大师,虚空战争的冰冷很适合他。而现如今他放松了下来。他摘下头盔,露出一团蓬松的粉红色肉,看起来成熟到可以从胸口溢出。一只眼睛闭着被一堆肿瘤遮挡,克罗修斯发现自己渴望检查这些肿瘤。
“和我同路吗?”卡尔加罗问道,肿胀的下嘴唇上挂着唾沫。
“看情况吧。”克罗修斯说。“你去哪里?”
“去那边,”卡尔加罗说,模糊地指着前面沸腾的灰尘和蒸汽的方向,“他的新宅邸。”
克罗修斯明白他的意思。原体从他的兄弟佩图拉博处获取了现在的住所,最后一搏的集结地。它曾经是一个港口。太空港。他们说它的规模是如此之大,甚至于突破了大气层边缘。占领此地使得战帅能够迅速投放泰坦并部署在皇宫城墙下蓄势待发。它依然是一项重要资产,一条再补给渠道,钢铁之主显然没有看出它的持续性价值,所以现在这个地方归他们了。
“我要去那儿,”克罗修斯说,“不过我更愿意步行。”
卡尔加罗咧嘴一笑。真是个步行的好天气。他用手背擦擦额头,在皮肤上留下一块黑色污渍,右太阳穴上的一个伤口顽固地拒绝愈合。反正那儿总比巨像门(Colossi)要好。真是一团糟。
“啊,它最终一定会沦陷的。只要我们坚持推进。优先级变了。”
“确实。真希望他们能告诉我们为什么,嗯?”卡尔加罗无情地笑了起来。克罗修斯以前从未见过他笑。
“我当时和凯法·莫拉格并肩作战,”克罗修斯若有所思地说,“经过马尔马克斯时(Marmax)他们试图阻止我们。我们屠杀了所有来者。最后他们蜷缩在高高的城墙后面,我们慢慢蚕食着壕沟。我们本可以把整个地方夷为平地。”
“所以有某种更好的计划。”
“你会这么认为的。”
坦克一辆接一辆地向前驶过。它们都很臃肿,大部分是棱角分明的斯巴达坦克,低悬挂的西卡然坦克,还有一些特种运输车和导弹车。每一台表面都布满淤泥,堵塞了进气口,污染了排气管。他们的指挥官们懒散地躺在敞开的炮塔上,盔甲上发动机油闪亮,布满血渍。一个单位左侧履带松脱,发出噼噼啪啪的响声,装甲也被击歪。它还没有被修好。克罗修斯猜测在某个阶段它会自我修补。现在看来事情似乎就是这么运作的。
“我太想成为第一人了,你知道吗?”卡尔加罗挠着下巴说,“头一个越过墙的。我想那是我们应得的。”
“现在看来这件事已经不重要了,是不是?”
“不了。很奇怪。不再是了。”他似乎短暂的感到了不安,“说实话,我甚至不怎么恨他们。我只是觉得这……很有趣。”
然后他内疚地朝克罗修斯看了一眼:“但请忽略我。我不是那个意思。”
克罗修斯笑了起来,拍了拍他的肩甲:“放松。我不是告密者。不管怎么说我的感觉也完全相同。”粘液聚集在他的喉咙后面。“仇恨是过去的事。现在这只是某种障碍,一个顽固和愚蠢的东西,需要被清理掉。在那之后——然后,我的老朋友——我们就可以开始重建。”
“但我什么都不知道。”
“不,我也还没预见到。也许只有原体能。不过我相信他。他会解决所有问题的,和以前一样。我们把这个地方推倒,把暴君埋在祂自己的墙下,然后那就是开端。我们再次创造它,但是按正确的方式。探险者,真理探索者,就像我们第一次被承诺的那样。”
卡尔加罗又笑了起来,这次他真的很高兴:“我喜欢这样,药剂师!我喜欢你说话的方式。当我们都到宅邸以后我们应该再谈谈。”
“一定。”
军械大师咯咯地笑着跺脚走开,去往他的大斯巴达坦克等待着的地方:“我保证让你信守承诺,别磨蹭时间了——他会希望你及时赶到的。”
“为了他的大计。”('For whatever he has in mind.')
斯巴达的引擎溅出油性污渍,然后履带翻动碾回土路。卡尔加罗抓着扶手爬上去重新占据了顶部炮塔的位置。克罗修斯目送他离开。他目送纵队的其余单位继续前进。这是一个庞大的队列,花了很长时间才通过。它消失后在泥里留下了犁沟,浑浊的水闪闪发光。
克罗修斯又开始步行。他的跛行更加明显。他的胃出现了新的绞痛,似乎有什么东西开始发酵。他头盔的战术显示屏开始失灵,前方的一切都变成模糊的像素。
他一瘸一拐地走着,开始哼着歌。一点曲调,一些对自己重复的东西,一些令人愉快的东西。
这令人着迷。眼前一切都尽在他掌握之中,等待着他前去发掘。(本章讲了死亡守卫军团三个人的故事,战士、药剂师、原体,但是取得的原文没有分段。这是我自己按自己理解分段的)
有时他认为自己已经对疑虑免疫。其余时间他感觉似乎已经不剩其他状态。
身为一名原体是什么样的?是肉体力量吗?是的,部分是。几乎无人能在战斗中与他匹敌,如今更少了。他现在掌握的力量太庞大——满溢着,从他伸展开来的盔甲接缝处喷薄而出。
但从概念上来说,远远不止如此。他们被任命为将军,而不仅仅是军阀。指挥官。统治者。在某个未实现的未来,他们会成为一个永恒国度的总督,随着文明发展致力于重新发现古代真理。有时,他利用自己现在拥有的赐福,甚至以为自己能瞥见那被毁灭的未来,仿佛拙劣的模仿。也许他的新主顾送了这些给他,仿佛某种黑色幽默。又或者他父亲为他打造的灵魂仍然有残留活跃在他破碎心灵的某处,努力恢复另一种因果关系,而这种关系也在一天天变得愈加疏远。
不过现在,他已经做了一笔交易。他把那个未来换成了另一个未来,一个比这个垂死的帝国所承诺的任何未来都更宏伟、更广阔的未来。每次他呼吸,眨眼,他都能看更多的可能性展开,每次都能看到新的辉煌。他忆起远在他出生前就发生过的事。他领悟了那些尚未发生之事,就仿佛它们已经被载入史册。
因为他已经做出了选择。这是重点。许久以来他谨慎的回避了它,因强加于他的无理要求而生闷气,因堆积在他道路上的不公而饱受折磨。他本可以滞留在一种优柔寡断的朦胧状态中,而非真正地拥抱他所释放的力量。他本可以遏制,只在需要的时候才使用巫术,从不投入,从不将自己沉入这冰冷、黑暗的水中。
但那种生活又能给他带来什么呢?他也许会更多保留的以前的自我。他也许能找到一种方法来克服矛盾,维持原来的状态和秉性,同时仍然摆脱既令他窒息却又保护了他安全的束缚。他的一些兄弟仍试图走上这条行不通的路。他想,佩图拉博可能会尝试最久。他注定会失败。任何尝试者都会失败。一旦你开始摇摆,无论多么轻微,你都注定要跌倒。
或者晋升(rise)。这么形容可能更合适。升魔(rise up),成为一名不朽者,在最高层次的舞台上发挥作用。他依然是位将军。他依然是名统治者。他现在已经没有主人了(和安格隆一样自欺欺人吧你们俩),除了某种意义上来说神是他的一部分,充斥着他,鼓舞了他,他亦是神的一部分,但拥有自己的意志和独立灵魂。这些是悖论。这些是赐福。
他可以把自己机警的头脑转向即将发生的事情。他可以开始想象一个没有帝皇存在的世界,以及这将意味着什么。一旦一切结束后,荷鲁斯会取代暴君的位置,顺位成为皇帝,并且从被他摧毁的王座废墟上统治吗?或许当共同的敌人被击溃,所有人都将走上自己的道路,就像失去了蚁后的蚂蚁一般,一切都会再次分崩离析吗?
如果荷鲁斯对未来有预见,那他也从来没向他提过。他在内心深处怀疑战帅已被现状所吞噬,为诸神的报复欲所填满,他看不到复仇以外的东西。只要暴君能被推翻,那就让银河系燃烧吧。一旦帝皇的喉咙被割断,其他一切也会迎刃而解。
不管事实怎样,他自己也不能那么漫不经心了。他不得不思考新时代的来临。他必须引领他忠实的子嗣们穿过它,确保没有新的巴巴鲁斯建立在旧的巴巴鲁斯的残骸上。他必须保证神明得到尊敬,它的领域从非物质界延伸到感官世界。福格瑞姆如果愿意,他可以放弃自己放荡的生活,安格隆可以尽情地愤怒嚎叫。而他不一样。他必须保证这些牺牲是有价值的(确实后来死亡守卫也是在腐化银河上最兢兢业业,拓展领土最广,业务最好的一个,都天灾群星了)。
现在他望向自己协助摧毁的世界。他孤身一人在备用港口的控制室中,这个巨大的高拱形空间布满残骸,在黑暗中茫然若失,而太阳在又一天的痛苦与挣扎中落下,西侧墙壁上的窗户在最后的余晖中火烧一般赤红,破碎窗格的边缘闪着金色。这里一切仍然散发着燃烧、油和金属摩擦的恶臭。军团,停留的钢铁勇士,几小时前按照他们主人的任性命令刚刚才撤出操作层。他猜测他们中许多人会选择在泰拉的其他地方战斗,不管佩图拉博做了什么。但不是在这个地方。这里现在是他的城堡了。这是他最终征服的那座山,一座最高峰,一个他将从这里摧毁不信者最后决心的地方。
当太阳疲惫地落到燃烧的西方,他看到战斗正在北部卡塔巴提卡平原(Katabatic Plain)上肆虐。伊赫特拉劳德笼罩在灰尘和烟雾中,但他的眼睛能看到死亡,比以往都要多,他感知了埃吉奥·莫蒂斯(l.egio Mortis)的野蛮进攻,横扫荒原直至引擎立在水星墙的阴影下。他看到了泰坦们的轮廓,和这种巨大的空旷比起来只是小斑点。即便死去的伊拉(Irae),它们中最伟大者,也不过一个微小的点,迷失在正在进行的战斗的巨大舞台上。在下方,在地面上,全是利维坦级,用它们的战角撕开空气,开始钻孔、切割和攻击,破坏他们和敌人之间最后的坚实防线。现在只余片刻。只剩一点点的时间,在倒计时中流失殆尽。神之机械的阴影下,无数的军队——信徒和雇佣军,自由军团的战士门,新机械教的生物,都在争分夺秒,都渴望第一个突破。
他自己也曾在前线。他曾近距离作战,用镰刀砍断不信者的脖子,偿还旧债的同时也完成了复仇。有些很难解决——甚至很痛苦,但账本还是被刮干净了。他本可以呆在外面,站在那些颤抖的墙基下,一旦碎石被推倒,他就准备爬上斜坡。但他没有。他的位置在这里。他的职责很明确。
他目光向上扫去,向西凝视,远离最初的缺口,穿过帝皇大结界上仍然闪烁的日冕。他观察到高高的塔尖,它们在其摇摇欲坠的保护下挤在一起,攀升的越来越高,直止他看到了他父亲私人领地的尖顶——在血腥的夕阳下一片漆黑——大天文台(the Great Observatory)、授勋广场(the Investiary)、霸权塔(the Tower of Hegemon)、巴布要塞(the Bhab Bastion)。
他伸出右爪,伸展利爪,仿佛他可以从那些堡垒中拔下山顶,抓住里面蜷缩的居民。他那被玷污的手甲环绕在要塞的矮墙上,这是其中最迟钝、最尽忠职守的仆人们的指挥中心。
“这是我现在带给你的礼物,我的兄弟,”他呼吸着,局促的腐蚀呼吸声里发出金属般的声音。“只有我才能带来的礼物,是神派我来这里,来此地的原由。”
他用钩状的手指捂住堡垒,掐灭它,用攥紧的拳头遮住它。
“你即将最终体会的知觉。你即将最后感受的情感。而你将会在灵魂深处明白,是谁把它带给了你,以及你为何始终无力对抗。”
太阳渐渐落山,整座皇宫淹没在黑暗中。只余恶行、掌控和无情的压迫。
“绝望,”莫塔里安咆哮道,他乃超越生死的恶魔王子,瘟疫制造者,希望终结者,“我给你带来了绝望。”